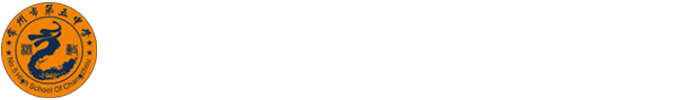戚逍逍
最初开始对班集体存在的意义进行思考,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李家成老师的一次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在美国访问学习的经历,提到美国的走班教学,由此引发了他的思考:“班级建设研究的中国贡献是什么?”他叩问在场的班主任们:你的工作对“育人”的价值在哪里?
美国在反思自身的走班教育模式时,会提到:从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理念来看,走班学习仅仅充当了“教学共同体”的角色,而班级管理模式则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现实的“微生活世界”,可以弥补个体对群体生活的需求。
但自由主义文化始终对群体生活、集体模式保有警惕的。
德国电影《浪潮》改编自美国的真实事件:1967年,美国加州一所高中,历史教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们明白什么叫法西斯主义,搞了一场教学实验。他提出铿锵有力的口号,“纪律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和“行动就是力量”,用严苛的规条束缚学生,向他们灌输集体主义,要求他们绝对服从,遵守纪律。学生们精神抖擞,穿上制服,做课间操,互相监督,步调一致地投入其中,他们很快凝聚成一个新的团体,他们给这个团体命名为“浪潮”。这个真实的事件戛然而止,40多年以后被搬上了银幕,对“极权主义”保持高度反思和自省的德国人把《浪潮》列为惊悚片,在影片中,被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文格尔老师,和他的学生一起,愈来愈沉溺在狂热的集体运动中,片中一个“浪潮”积极分子学生道出了一个理想的集体生活:“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集体主义带来的高效、荣耀以及共同承担很容易使得身在集体中的一员寻找到归宿感与满足感,可以说,集体主义并非一种灌输形成的意识形态,更多是心理需求的投射: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里写到:“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狂热群体的根源在于没有自我认知价值感,当一个人并没有或者无能力去发掘出自己内在真正的自我价值的时候,他就开始攀附于其他人群,他的存在感是通过人群获得的。
平时渺小失落的个体,在集体的力量中获得满足和慰藉,是我们对集体生活的一般期望,而在这一的期望过程中,对集体产生的离心和反作用力的个体,会被其他集体成员共同排斥。在即使没有领袖人物要求的情况下,这个集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成为了一个纪律的自觉维护者。有这样一个身边真实的小故事:就读于南京某重点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一天回家对妈妈说,今天班级公开课上,某某的铅笔盒掉在地上了,你说,她是不是丢我们一(X)班的脸?
集体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是班级中维持集体秩序的一员,检举揭发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以集体荣誉的名义要求所有人保持一致,如果对王朔的自传体小说《看上去很美》记忆犹新的话,就能发现:方枪枪所经历的童年阴影雾霾未散。
我们对中国班级管理模式的反思于此:当学生从家庭走向社会,学校应当是两者之间的纽带,然而我们的班级生活侧重于对“集体生活”的营造,当学生从个体家庭剥离,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个性化的教育引导,学生的社会独立性依然很弱,更多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数字符号淹没在集体中。当然,会有很多班主任表示反对:在各种活动的开展中,包括我们德育工作的重心,都是在唤醒学生个体意识,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
在集体的无意识中追求个体的有意识,此事不是不可为,但很多时候是二律相悖的徒劳:我们用集体荣誉激励学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设定了异见者是对集体的背叛。“没有集体荣誉感”是对于行为不趋同者的最合理判决,但事实上,从个体而言,他做的只是他自己,并无原罪。凝聚力越强大越优秀的集体,给个体带来的依赖感和荣誉感越多,对集体的游离个体越不能容忍。“集体”可能是平庸者的天堂,也可能是优秀者的桎梏,更让失败者无处可遁,遭受个体失败和集体迁怒的双重压力。
集体的优势在于高效、速成;然而百年树人,作为“慢的艺术”的教育,是不可能通过急功近利的集体跃进实现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然而几乎所有教育评价体系都是阶段总结性的,没有哪一位小学老师的评价基于他所教的孩子的高考成绩,也没有哪一位高中老师的教育成效评价基于他所教学生的终生,集体建设的速成正迎合了如今的教育评价体系,所以即便班主任专业化的课题,也更多是围绕班级管理艺术,而非从根源上思考班级存在的意义。
真正对学生个体的解放,其实是破除“集体”意识的走班制。在中国教育改革转型中,走班制的实验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果缺失了班级组织形式,如何弥补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过渡以及个体对群体的心理需求?又如何解决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与德育相关的一系列困惑和问题?教学与德育长期剥离的班级模式下,我们的课程教学是否也要随之跟进?……这些问题并非无解:社会活动纳入课程、课程教学渗透德育、建立私人定制的导师制度等等,都是可以期望的未来。
而在践行之前,“班级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依然是需要勉力跟进的话题。
《浪潮》被列为惊悚片,我们的教育结果未必如此极端化,但明显带有计划经济时代遗风的“集体”意识,与教育改革中对学生发展目标的要求格格不入:在强大的“集体”意识里,如何走向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质疑精神、独立思想的学生个体?社会责任意识源自强烈的个体自觉,依靠依附形成的失落者联盟也许具有超出他个体本身的能量,但缺乏自省和批判的趋同,会导致任何一种可能,可能指向“善”,但谁说一定不会指向“恶”?而脱离了“集体”以后的个体,又如何在社会孤岛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如果班级存在意义还在指向集体意识,就不得不面对上述问题。
不以“集体”的名义,班级还有可能是什么?
我认为,目前,班级最合理的定位是“团队”,这一社会化指征突出合作与个体竞争,不强求归属感和统一性,强调个体的角色定位,即“在班级里找到最适合你的位置,发挥你个人所能”,不追求集体定位,重视个体荣誉和发展。在评价体系中,要求弱化班级数据指标,强化个体发展前景。
其次,班级最理想的目标是“微生活”,提供一个不同于家庭的群体生活环境,分享成长经历,注重学生个体的社交和参与,通过对“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的不同体验,建立社会生活秩序和规则意识,收获个体不同的情感体验。
在如此定位的班级中,班主任是团队活动的组织者,是“微生活”的陪伴者,是班级生活秩序的监督者,是班级社交活动的协调者。
对班级管理中“集体意识”的反思源于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亦是“走班制”教学管理模式接轨的必须——一个在集体中扮演顺从和无意识角色的个体,是无法断然走向自我学习管理之路的,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实现班级定位的转型,以便学生实现自我认知。在实行“走班制”教学管理模式之前,这是对班级存在意义的一些建议性的思考。